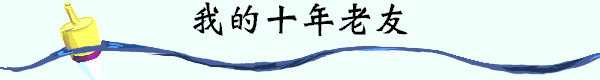|
|
|
□ 我的十年老友-台北樹蛙 .楊懿如. 【原載於82.5「鄉間小路」】 |
|
| 和台北樹蛙結緣,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十年前,當我還是台大動物系三年級的學生時,基於好奇心和學長的推薦,我修了一門由王慶讓副教授開的兩棲爬蟲學。這門課安排有野外實習,記得有一次實習是安排在12月的一個稍帶有寒意的冬日,到木柵老泉街採集青蛙。 |
 |
那天,臨出門前我心裡還嘀咕著:冬天那來的青蛙,只怕會白跑一趟。到了實習的地方,沿途果真看不到幾隻青蛙,直到王老師帶著大家到一塊堆著稻草桿、已經休耕的稻田。只見他熟悉地翻開稻草堆,映入大家眼裡的竟是隻躲在自己挖的洞中,張著大而無辜的眼睛,害怕地望著我們的小青蛙。王老師告訴我們牠叫台北樹蛙,並小心地拾起這隻體長不到4公分大的樹蛙放到我手上。初接觸時的冰冷、柔軟感覺讓我有些害怕,但漸漸地,我可以感覺到牠變暖和了!而體色也由原本在洞中的褐綠色轉變成美麗的翠綠色。當我小心地放走牠時,也暗下決心一定要再一次拜訪牠。 我並沒有食言,一個禮拜之後,我和當時還是男朋友的我的先生—李鵬翔,就騎著腳踏車再一次造訪牠,也開始了我的研究歷程那一次我們不但找到台北樹蛙,也找到埋在洞中,潔白鬆軟有如綿花糖的台北樹蛙泡沫卵塊。幾次粗淺的觀察下來,我和李鵬翔對這美麗的小動物的好奇心愈來愈濃:牠們為什麼要在寒冷的冬天產卵?牠們又是怎麼產下白色的泡沫卵塊?於是在大四那年,我們就請在民國67年為台北樹蛙命名,並鑑定其為台灣特有種的王慶讓副教授當我們的學士論文指導老師,研究台北樹蛙的生殖行為及生態。 那一年,我們每星期到木柵老泉街調查一個晚上,將每一隻捉到的樹蛙都以「去趾法」做個體標記,並測量體長。我們在發現的每一個台北樹蛙巢洞及卵塊旁都插有一根由竹筷和塑膠布做成的旗子,用來記錄和追蹤之用,並將位置標示在地圖上。剛開始調查的時候,我們曾把雄蛙和雌蛙帶回家裡,看牠們怎麼產出白色泡沫卵塊。結果我們發現,泡沫卵塊是由雌蛙慢慢地、交互地雙腳踢打,如同我們把沙拉油打成沙拉醬般踢出來的。這過程相當緩慢,常歷時4到6小時。產完卵後,雄蛙先行離開,留下雌蛙再踢打數分鐘,最後終於拖著已減輕1/3到1/2體重的身體,疲憊而虛弱地離開。
但這過程我一直都沒有在野外看到,直到有一天我們決定做一次整夜的觀察。那一天接近午夜的時候,我們坐在一座小土地廟前啃著冰冷的麵包,我邊吃邊對李鵬翔說,我真希望待會兒到田裡,一掀開稻草就看到一對台北樹蛙在交配。不知道是感動了土地公還是台北樹蛙,我這個願望實現了﹗ 那一天我太興奮了,凌晨回到住處休息時,竟久久無法入眠,耳裡聽到淨是台北樹蛙低沈而悠揚的「呱—呱—」叫聲。這種失眠的感覺在我往後的6年野外研究歷程中不斷地出現,最後竟也習以為常,當成職業病了。
第一年的學士論文研究雖然很簡單,但也有粗淺的結果。我們發現台北樹蛙的生殖活動和雨量、溫度有很大的關係。牠們固然是在冬天繁殖,但太低的溫度(例如5°C以下)也會抑制牠們的活動。18°C左右的氣溫及下雨天,是牠們最活躍的時刻。所以台北樹蛙僅分佈於受東北季風影響而冬雨綿綿的台灣北部,而不見於冬天常有乾旱之苦的台灣南部。 雖有初步的結果,但我和台北樹蛙的「實際」接觸並不多。因為捕捉、測量的部份由李鵬翔處理,我負責記錄。所以半年的調查下來,我連捉台北樹蛙都不太敢,生怕捉太重會傷了牠,太輕又會讓牠跑掉。這種情況直到我考上研究所碩士班,必須獨立作業後才有所改進。
林曜松教授是我碩士及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第一次找林老師談論文題目時,林老師開門見山跟我說,他沒有指導過學生做青蛙生態的研究,但他願意收我,因為他訓練學生的原則是要能獨立思考。從失敗中學習經驗。此時我自許已經做過學士論文,只要在同一個地點重複再做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不應該有問題。誰知道木柵的那塊稻田竟改種蔬菜,在不斷地翻耕及施放農藥的情況下,族群量急遽地下降,我被迫要在更換實驗地或更改題目的兩種選擇下做決定。我曾嘗試過研究關度平原的候鳥,但在做幾次「早起的鳥兒」之後,我覺得我還是比較適合研究「夜行性動物」,所以又回到台北樹蛙這個題目。 在還沒找到適合的實驗地之前,我在實驗室裡佈置了一個適合台北樹蛙棲息,有草有水有覆蓋物的水族箱,然後進行一些簡單的實驗。首先我想知道剪掉腳趾的永久標記法會不會影響台北樹蛙的行動能力,結果發現牠們的傷口癒合能力很強,很少發生感染的情況。而為了能在做行為觀察時,不提起樹蛙也能知道牠們各自的號碼,我在牠們身上綁了一個號碼牌。剛開始我選用一般的縫衣線和膠帶黏成的牌子來做號碼牌,結果發現縫衣線太硬會傷牠們的皮膚膠帶遇水會脫落。最後幾經測試之後,我選用將柔軟的綿線縫在白色塑膠布上來當號碼牌,然後再繫到牠們的腰部。綿線泡水太久會爛掉,所以號碼牌要不斷地補充。幾年下來,我做的號碼牌不下數千個,這實在是當初設計時所料想未及的。
研一的許多漫漫長夜,我就是在實驗室的水族箱旁和台北樹蛙一起度過的。我看著牠們用前肢往前推、後肢往後踢,以身體為中心,轉圈圈的方式築巢;也看到母蛙受雄蛙叫聲吸引主動地爬進雄蛙巢中進行交配的過程。和牠們相處的時間愈長,愈堅定我要瞭解牠們的決心。研二很快的就到了,我也必須面臨實驗地的問題。最後我選擇了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面天山區步道旁,被高大芒草圍住,所以一般遊客注意不到的一個人工挖掘水池當實驗池。 第一次一個人上山,是在民國75年的教師節。那天下著傾盆大雨,我一個人孤獨地撐把傘捧著「溫度自動記錄儀」上山安置。才爬了200多個階梯,我心裡就開始有兩種聲音在交戰:回去吧!下這麼大的雨,改天再上山也不遲。但另一個聲音告訴我,凡事起頭難,我只要能熬過今天,以後就沒有什麼好恐懼、畏縮了!就這樣,我一步一步連休息都沒有地爬完1300多個階梯到達實驗池。當我見到實驗池時,我知道我的研究一定會成功,因為我已經克服了最難排除的心理障礙!
為了方便觀察,免除天天爬階梯之苦,我在實驗池附近的「三聖宮」寄宿,每星期天下午上山,直到星期五下午才回學校上課。在山上期間,每個晚上都有實驗室的同學、助理,甚至我妹妹的男朋友輪流上山來陪我進行觀察。剛開始的前半個月,我忙著替實驗池畫地圖,同營釘和塑膠繩把整個水池畫成64塊方格,以方便標示台北樹蛙出沒的地點。然後我仔細地把芒草舖在岸邊,盼望台北樹蛙能來到底下挖洞築巢。但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我注意到蛇的數目比青蛙還多。有一天我心血來潮:為什麼不放一段台北樹蛙求偶聲來誘引她們呢?叫聲一放,馬上聽到前方芒草一陣悉索的聲音,然後有兩隻母蛙從芒草葉上跳到地面,並急急地跳往錄音機的位置,最後索性在錄音機上爬來爬去,牠們心裡可能在想:我的青蛙王子呢? 皇天不負苦心人,在1O月19日那天,我終於等到第一隻台北樹蛙雄蛙駕臨我為牠們精心佈置的實驗池。那天我如往常一般把塑膠布舖在乾涸的池底,然後放我的背包和一些實驗用小工具。雨和台北樹蛙一起悄悄地來臨,我忙碌而愉快地捕捉、測量、上標記,差點忘記放在池中央的背包,於是我把塑膠布往岸上撤,邊撤邊想,台北樹蛙在巢淹水後是不是也會往岸上撤退再來一個新巢呢?翻開舖在地上的芒草一看,有隻樹蛙已經往上在築第三個巢了!這是我第一次發現牠們的小腦袋瓜還不笨呢! 幾天之後,我發現,牠們豈只不笨,還狡滑得很。在蔣公誕辰紀念日那天,我決定做一徹夜的觀察。那夜大約有5、6隻台北樹蛙築巢鳴叫。但就是有幾隻樹蛙不叫也不挖洞,靜靜地坐在鳴叫雄蛙的附近,我覺得很奇怪,所以就特別注意牠們。事情發生了!就在鳴叫雄蛙獲得交配停止鳴叫之後,牠們悄悄地爬進方才鳴叫雄蛙的洞中。企圖和辛苦鳴叫才獲得母蛙青睬的雄蛙一起分享母蛙。這讓我恍然大悟,原來以前在水族箱內看到的一隻母蛙和二隻公蛙一起配對產卵的現象並不是人為環境所造成,而是較弱勢的雄蛙(年輕小型個體或在池子已經待了一些時間,體能耗盡的個體)企圖獲得交配成功的一種策略。
爾虞我詐,弱肉強食是動物求生存的現實面,小巧的台北樹蛙也不例外。一般來說,雄蛙之間通常都能和平相處,縱使巢與巢之間的距雜僅有5公分也互不侵犯。但是在雄蛙密度比較高的時候。有些個頭大的雄蛙也會耍大哥,硬是侵入其他雄蛙的巢中。此時巢中的雄蛙會發出「《丫ˇ」嘶啞的聲音,用來警告驅逐不速之客,如果這種溫和的警告無效,兩隻樹蛙會以前肢交纏,有如摔角的方式打架,並互發出「《ㄚˇ」接觸叫聲。打架常持續1至2個小時,雙方互有勝負。
平常我晚上6點到12點進行行為觀察,早上8點再到實驗池記錄前一夜雄蛙築巢位置、新產的卵塊數目及地點。並觀察卵在野外的發育情形。母蛙一次產300至400粒卵,卵在一到兩星期後孵化或蝌蚪,此時蛙巢變成暫時提供蝌蚪生活的小水池,待大雨再將蝌蚪沖到水域裡。在面天山區,由於水溫較低,台北樹蛙的蝌蚪期可長達3個月以上,而小蛙也僅在每年的3至4月出現。 初變態的小蛙,體長僅1.5公分,一年半後,可長到4公分並達性成熟。根據我連續6年對台北樹蛙進行的標記再捕獲研究發現,牠們的壽命可達5年,而且每年回到同一個生殖場所繁殖。由於我每星期至少對實驗池裡的台北樹蛙做一次捕捉及標記,所以我幾乎認得池裡的每隻雄蛙,也知道牠們的年齡及成長過程。在牠們的社會裡,我覺得最有趣的現象是,雖然她們的繁殖期長達半年(10月到次年3月),但雄蛙利用水池進行生殖活動的時間卻是長幼有序的。也就是說,年長的雄蛙先進入水池,年輕的雄蛙比較晚到,年年如此,未曾改變。
回首過去的十年研究歷程,從玩票到專心投入,完全是因為台北樹蛙不斷地帶給我求知的喜悅。感覺上,我好像在拼一張台北樹蛙的拼圖,從零零碎碎的片斷,拼出一幅美麗、完整的圖畫。往後的日子,我還是要持續拼圖的工作,拼出全台灣所有的青蛙。而台北樹蛙仍將是我的老友,我一輩子的好朋友。
|
|